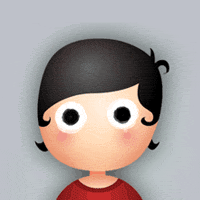我要回上海(大结局)
第十章 不甘
记得那天是有月亮的。
惨白的月光照着河边黝黑的树林,也照在粼粼微波的河面上。
快到河边的时候,我没有在上次她拉琴的地方看到琴琴,心里一紧。
还是黑皮眼尖,他已经大喊出口:
“琴琴你要干什么?站住!不许再往前走了!”
随着他右手指着的方向,我终于看见,河滩上有一个人影,正缓慢地向河心蹚去。
不要啊!
所幸是枯水季节,这河要到河心才有齐胸深,人才有可能站不稳,我俩有足够的时间赶上。
只见黑皮三步并作两步,很快就抓住了琴琴的胳膊。随后我也赶到了。
她想犟,又明知怎么犟也犟不过我们两个大男人,她只有委屈地抽泣起来。
这时,我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,拉着她的手,将她的双臂分别架在我俩的肩头,把她拉上了河岸。
大家伙也都赶到了。
“琴琴,我刚才有什么话说得不适当,你骂我啊!”这是黑皮的声音。
“哎呀呀,裤子上下里外都湿透了,还不赶紧扶她回屋换衣服。”珍珍说,“阿雯,你赶紧先回屋,帮她把干净衣裤找出来。”
“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抬?”小弟怯怯地询问。
“都不要走!”这是阿廉沉稳的声音。“我们要帮帮琴琴,今天是个绝好的机会。这半年来,我们都想帮她,可是一直没找到好的机会是不是?今天机会来了,我们绝不能轻易错过。”
“什么机会?”
“如果我们现在扶她进屋,帮她换好衣裳,再安慰几句,那这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了。也就是说,我们的琴琴白白地下了一趟河。”
“我们还能怎么做?”
“这件事我们要让当地领导真实地看到。这些年来,他们最怕知青什么?就怕我们出事,出人性命,我们何不逼他们一逼呢?”
“这个有道理,”黑皮说,“我要不是那样去逼黎主任,黎主任也不会轻易松口。”
琴琴似乎想说话,被阿廉一个眼神拦住:“琴琴,从现在起,你一句话也不要说,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听我们的。我们是在帮你。”
在阿廉的从容指挥下,大家找来了一块铺板,让琴琴就这么湿淋淋地躺下,上面盖一条薄毛毯,干净衣物让阿雯拿在手里,到时候再换。
一群人抬着琴琴向大队部进发。
还没走多远,黑皮说话了,“一样弄,干脆弄弄大,我们把琴琴直接抬到公社去算了,大队部能解决问题吗?”
好主意!直接去公社。
黄沙公社的办公楼居然灯火通明。
原来明天公社里要开“学大寨双抢动员大会”,这会儿,正在开党委扩大会呢。
好极了,领导班子成员都在,更容易当场作出决定。
听说有知青自杀,大家都下楼来到了大门口。
头头们都认识琴琴。她是公社里数一数二的文艺骨干,谁都知道她小提琴拉得好,还代表公社去县里汇演呢。
几乎每个人都附下身去问琴琴怎么了,但琴琴按照阿廉的吩咐,一言不发。
大家只好来问阿廉。
“我们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,反正就是想不开了。”阿廉说了起来,“我们把她交给公社,是因为最近她老是一个人往河边跑,我们都有自己的事,不可能老看着她。如果再出事,我们可承担不起责任。再说,琴琴的父母把孩子交给了你们贫下中农,让她来这里接受你们的再教育,你们应该对她负责到底的啊。”
“对呀对呀,”其他知青拼命附和。
第十一章 不安
“好了,我们把人交给你们了,我们回去吧。”
“不要这样嘛,”公社书记终于说话了,“这样,我们的妇女主任小罗先把琴琴扶到房里,帮她把湿衣服换了。谁去叫一下卫生院长老邓,叫他来出个诊,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。你们上海人也不要急着走,我们也没说不管啊,来来来,就在这里坐会儿,抽支烟。”
那书记顺势散了一圈烟,自己也点了一根。
“这样,也巧了,我们班子的同志正好都在,那我们就上去抓紧议一下,能有个结论就更好。”
开会的人又上了楼,阿雯和珍珍则跟着去了妇女主任小罗的宿舍。
黑暗中,我轻轻地捶了一下阿廉,“看不出嘛,小子,每逢大事有静气啊。”
阿廉谦逊地摆了摆手,“你猜,会是个什么结果?”
“说不好,”我心里很乱。我极希望琴琴能有个好的改变,却又不希望通过这种逼宫的方法。
“以后我们都回上海了,会不会把琴琴调到公社上班?”这是小弟的猜测,“这个他们是可以办得到的呀。”
“我看顶多也就是这样了,也可以说,这已经是琴琴最好的结局了,她又不肯病退,”黑皮说。“总不见得公社马上把她送回上海去吧?”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,妇女主任小罗出来了。
她说,书记他们还要接着开刚才那个没开完的会,就不下楼来了。
公社的意见由她来转达。
“大家放心,公社绝对做到对琴琴负责到底。今天太晚了,明天一早就争取与她父母取得联系,告诉他们,由我们公社出钱派人先把琴琴送回上海家里调养一段时间。”
“啊?真的就直接送回上海啊?”黑皮很惊讶。
“那以后呢?”
“以后么,如果恢复得好,她本人又愿意再来这里锻炼,我们当然还是欢迎的。”
“那如果她不愿再来这里了呢?”
“不愿来的话,她就安心在上海家里继续调养,需要什么手续,我们公社都会帮着办好的。好吧,你们也辛苦了,如果没有其他事,都早点回去休息吧。”
回村的路上,大家都沉默不语,与来时的愤慨激昂恰成鲜明对比。
走到河边的时候,黑皮终于摒不牢了:
“册那,这叫什么事啊,我们几个动足脑筋,吃足苦头,我手指也没了,大模子还在医院躺着呢,好不容易有了点头绪,她往河里那么一蹚,就蹚到上海去啦?而且她只要坚持不回来,她很可能比我们几个都要早一步重做上海人啊!”
黑暗中,大家的眼神都很茫然。
我也很茫然,本来,万一他们都回了上海,琴琴和我还可以在这里相依为命。
现在,我是不是也要学学小弟了呢。
尾声
1991年,上海人艺的一位编剧创作了一部五幕话剧,描写了云南知青的生活。
剧中主角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女知青。据说那女编剧本人就是云南知青,也许那女主角就是写的她自己。
也许因为我也是知青,我有幸被邀请去观摩演出并在座谈会上发言。
我觉得琴琴一定会喜欢,便约了她一起去看戏。
一晃十几年过去,大家都各自忙着找工作,读大学,娶的娶,嫁的嫁,生儿育女后就更忙了,几乎没怎么见过面。
人就是这样一种健忘的动物,重新做回了上海人,当年的痛苦已然忘得差不多了。
再来看知青的戏,也只是带着一种旁观乃至娱乐的心态了。
当年的人艺院长沙先生很有市场意识,他很早就懂得“互动”了。
每晚演罢,他都要在门厅里放十几张椅子,请些嘉宾来聊聊,围观的观众都可以自由发言。
墙上贴满了观众自发写的影评观感。我和琴琴到得早,便随意浏览起来。
我们看到其中有一篇文章吸引了很多人驻足,也挤进去看。
那是一个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女知青托人贴在这里的。
她已经没有力气来看反映知青自己生活的戏了。
她得的是一种血液病。她写道,当年也是看着别人都病退回上海了,自己怎么找也找不出毛病来,情急之下,竟将点灯的煤油用注射筒注入了自己的静脉。
看到这里,那些日子一下子就回到了眼前。
一旁的琴琴的手指透过衣袖,似乎要掐到我的肉里去。
我们赶紧走开去。
原来,苦难既还没过去,也不会结束。
(全文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