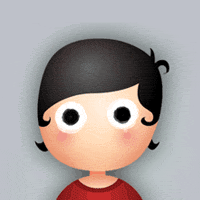【学礼堂访谈录】校经勘史,簿录索引——程远芬教授访谈录(三)
校经勘史 簿录索引
程远芬教授访谈录
【三】
上期回顾:
下期预告:
相夫教子
读书明理
整理古籍
王锷:您还帮着王先生整理过《二十四史校勘记》中的《三国志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隋书》《新唐书》校勘记,据杜老师跟我讲,张菊老的《二十四史校勘记》,您是整理的最多。当时那么忙,怎么会整理这么多的校勘记,谈谈相关情况。
程老师:张菊老的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》,应该是都有,但是历经多年,只留下来十七部史书的校勘记。那么在十七史里边呢,我完成了五史。一个是《三国志》,最先做的是《三国志》,后来是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隋书》,还有《新唐书》。其中《新唐书》的部头最大,有十几册的原始校勘记,整理后商务印书馆印出来是上下册。
王锷:这五部史书的校勘记,加起来量不小啊。
程老师:这个量很大,大概有几年的时间。我一直就是在一部史书一部史书地覆核、整理。原因怎么说呢,当时王先生找人并不是很方便、很容易,再就是他看我做得还不错,经常是非常客气地问:“程远芬同志,你能不能再做一种啊。”我是愿意做的,因为我在文学院教课,教的是古代文学,文史也不分家。借这个机会补补课,对于史书多一些了解,那对我的教学、对我学术的拓宽路径,还是有帮助的,所以我也乐意去做。最后十七史校勘记,我自己呢,整理了五史,大约花了有六七年的时间。因为张菊老、蒋仲茀他们都是毛笔的手稿,有些字要仔细辨认,要通过武英殿本来查,根据原书,往往找到原文才能够弄清楚这个比较草的字是什么字。那是早期,后来慢慢熟悉了他的字体、笔迹,就方便一些。
王锷:这些留下来的校勘记全是张菊老的笔迹?还是有其他人的?
程老师:有张菊老的,更多的是蒋仲茀先生的。
王锷:那么做这些校勘记,您不能只整理校勘记,要对这五部史书从头到尾也要看。
程老师:也要看。
王锷:所以量是不小的,您做的这五部史书校勘记下来,也有上百万字吧?
程老师:因为这个校勘记,商务印书馆后来是用我们的手写本影印出来的,没有排印,所以具体的字数有多少就没法确切统计。但是这个校勘记对学术界影响还是非常大,而且对于我的学术生涯,我觉得影响也大。影响大,就是感慨于张菊老在当时做这个工作。从出版社的角度,他是想提供稀见的本子,也是用这个来吸引读书界、学术界的注意。我觉得既然是这样,你用宋本、你用元本,原本那越真实越好。但事实上,在我们整理校勘记的时候,发现在很多地方改了。就是宋本不是这个样子的,他改了,改了呢,对学术界也没有交代。而事实上,有的地方,一改改20多个字。我当时也很纳闷,也跟泽逊探讨这个问题,就是张菊老,他也是个学者,虽然说他是个出版家,或者说出版商,但他是个学者呀,为什么要这么做?因为他误导了学术界很多年,以为这个地方宋本就是这样子,岂不知不接触这个校勘记,你就认为他宋本是这样,但是接触了才知道,这恰恰是证明张菊老他们在影印过程当中就直接改了。可读者不知道啊。直到有一天,你看到宋本的时候,欸,怎么和张菊老那个百衲本不一样?看了这个校勘记,你就明白了,凡是要改的地方,张菊老都批个“修”字。有时候还批“重修”,这是说这个字已经修改了,但跟宋本或元本字体风格出入太大,张菊老就让人再重新地把这个字修得跟原版本的字体风格一致。所以我看了这一点,也是感觉到,身为出版家的学者,先是以学术来吸引学术界的注意,最终目的是盈利。也就是说,盈利第一,学术次之。
王锷:这种情况很多。
程老师:很多,我记得《史记》是修了2000多个字,《三国志》是修了1000多处。当时有统计,具体数字记不住了。这个修字情况还是很大。
王锷:就是从他校勘记反映出来,凡是他修过的地方,肯定是注了“修”字。
程老师:那只是在他的校勘记里边。
王锷:他在校勘记里边说明是修了,但是百衲本里边是找不到痕迹?
程老师:找不到痕迹,你看不出来。你修得不像,他让你重修,那读书人不就看不出来了嘛。
王锷:就是几乎每一部书都应该在几百处甚至几千处。
程老师:当然也看书部头大小了,基本上都在上千处以上。泽逊的《史记》,我知道是修了2000多处,《三国志》印象里是修了1300多处。后来我校的其它的都有。你看那个《元史》校勘记,下面修修修,凡是修的都是改字。
王锷:现在,就张菊老所做的这些事情,有没有人专门写文章来谈这些事情?
程老师:我们在做了这个工作以后,我们就写文章,我和泽逊都写了文章。
王锷:都专门谈过这个问题。
程老师:是的,专门谈过这个问题。我记得我的那一篇是发在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上,后来在台湾的《书目季刊》上也发了一篇。
王锷:也只是举例谈了关于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的一些情况。
程老师:一是谈《二十四史》的情况,二是谈宋建本《三国志》的情况。
王锷: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,也解答我脑子里面一个疑惑。就是我在做这个《礼记郑注汇校》的时候,最早是准备拿《四部丛刊》影印的绍熙本《纂图互注礼记》来做底本的。因为做这个事情的缘起,也就是拿这个本子给学生来上课,发现很多的错。但是大家都知道《四部丛刊》影印的是宋本,是很好的。结果后来等到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把这个绍熙本重新印出来以后,当我一对的时候,就发现有300多处差异,而这300多处差异,原原本本你去读是读不出来的,他修得是一点痕迹都没有,但是当你去一对的时候,发现这个字是改过的,换成另外一个字了,但是一条都不讲。和您刚才说这是一回事,是一种做法。所以呢,在很多年,大家都认为《四部丛刊》影印的宋本就这样。从我们现在学术角度来说,《四部丛刊》本就《礼记》而言,显然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。所以我在做《礼记郑注汇校》时,我是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的宋本做底本,叫它为宋本;《四部丛刊》影印者叫《四部丛刊》本,我想这样更合理一些。也就是说,当时他做的很多书大概都有修改的痕迹。
程老师:我现在不知道,赵生群先生与你们南师大《史记》修订团队,在当时用没用百衲本的这样的一些信息,在你们整理《史记》的时候啊,这个《史记》校勘记商务印书馆早已经出版了,出版在2000年前后。
王锷:最后汇总是赵老师来汇总,我听他讲这些东西他都是对过了的,应该是吸收了的,也反映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。但是怎么处理的,是赵先生统稿的,大概是这样。那么程老师,您整理这五种史书的校勘记,对您来说,最大的收获有哪些?
程老师:就是补足了我在版本学上的缺憾,再一个是校勘学上,大大的丰富了校勘学方面的一些知识,尤其是一些例证。再一个就是对这五部史书的全面熟悉。
王锷:举例谈谈。
程老师:首先是对于底本的修改问题,外人不知道,还把它当宋本来看。而事实上,它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一个版本。那么在后来讲述文献学的版本、校勘部分的时候,这样的一些切身的感受和体会,也会放到教学过程当中。就是说整理这五种书,除了让我对这五部史书本身,从面上有了一个接触。同时呢,在版本学上、校勘学上,对他们的认识,在学术上的提升,还是有很大帮助的。当然有一些副产品,有的写成了文章,有的就变成了资料、卡片放在了那,没有时间来进一步地梳理。
王锷:可以出个论文集。
程老师:其实有的光是资料堆在那儿,也还没有写成文字。
王锷:把一些写成文字的,包括一些资料,把它整理整理,也可以出一个论文集。
程老师:也可以。记得关于《三国志》的,在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上是发了,也挺长。当时编辑们说,把后边的几个都写出来,他们都给发。但是后来的很多事情都是推着走,所以放下就放下了,就没有再实现了。
王锷:您整理过钱大昕的《十驾斋养新录》,还有他的序跋等等,请您谈谈整理情况。
程老师:钱大昕的序跋,《竹汀先生日记钞》,《十驾斋养新录摘钞》,这个是收在《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》第三辑。
王锷:就是杜老师主持的那一辑。
程老师:他主持那一辑的里边的一种,这种是非常难。
王锷:钱大昕的东西不好点,我知道。
程老师:确实非常难,请教过很多师友,包括请教刘晓东老师。有些就是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点法。因为他引用的东西,我们今天的学识很难达到。就是在点校过程中,也让我充分地对乾嘉学派领袖级的人物,他们的学术水平,他们的读书之多,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所以面对他们这些东西,往往也感觉到很惭愧。今天我也是老师,大学老师。我觉得面对钱大昕们,我真是感觉到自己做一位老师是不够格的。点这个很难,当时也参考了很多书,包括一些大家在过去点校了的钱大昕的著作,发现大家点校的也有错误。从而也进一步感慨,乾嘉学派的学问之深之细,做学问之难。
做这个工作花时间也不少,书后面也编了索引,那这样就是大约花了两三年的时间。我觉得是每做一项工作都有学术上的收益,这是让人最开心的一件事。
王锷:那么还有一种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,也是您点的?
程老师:也是我点校的。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是当时张菊老先生的哲嗣张人凤先生,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一个项目,叫“张元济古籍题跋书目汇编”,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是其中的一种。这个也不好点。里边尤其是涉及经学、礼学者,也是很难、很头疼的。但是也从来没有人点过。在点的过程里边,加上整理过百衲本《三国志》,就发现了这个张元济先生在《校史随笔》当中引用的例子,恰好就是和我这一块内容相重叠。我就回去查看《校史随笔》,结果发现张菊老正好弄反了。我曾经跟张人凤先生提起过。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搞了一套《蓬莱阁丛书》,全是名著导读,其中就有张菊老的《校史随笔》,《校史随笔》的导读就是张人凤先生。他在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序,在序里面,他还提到我,对于《校史随笔》哪个地方有贡献。张先生的这个行为让我还是很感慨,很提携后进,而且对学术是实事求是,很负责任,不为尊者讳,不为长者讳。作为张菊老的后人,能够这么做,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王锷:据我的了解,在版本目录学著作中,我认为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至今应该是版本目录学的代表作。您认可吗?
程老师:我认可,在你昨天说要采访我的时候,我就在想这个题目,我就在想,这个书要不要单独拿出来,再充实一下,补充进一些相关的信息,单独出。
王锷:这个书是和另外一种是合在一起出的?
程老师:它是丛编里边的一种。
王锷: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,他叫宝礼堂,和《礼记》有关,我对他里边所写的《礼记》那一条是反复读过,甚至是逐字地来抠过他的东西,当然,我把现在八行本对了以后,发现张先生也有搞错的地方。但是不可否认的,就是说,这本书作为一个版本目录学著作,它的体例是最全面的。目前我们似乎没有著作的体例能够超越它。
程老师:张先生毕竟是行家,他在体例的构建上还是非常完备。
王锷:就是从它的书名,包括一般的书名、作者、卷数、页码、刻工、藏书等等,全方位地介绍。我们现在能想到的,似乎他都弄进去了。
程老师:我也认可这一点,因为他比我们现在要早很多年,他当时的条件也不如我们今天便当。我整理这本书大概是二零零几年的时候,假如是今天回过头来,重新来做,可能做得会更好一些。
王锷:要不可以修订重做一下。
程老师:是啊,我昨天下午还在想这个书,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,要不要拿出来重新弄一下。
王锷:可以重新弄一下,可以补充一些内容。比方说,就八行本《礼记》里一条,张先生是把它分成了原版刻工和修版刻工。经过我的核查,恰恰有搞混的,甚至他有漏掉的。他当时一个老先生在那做,能够做到百分之九十五六,已经很了不起。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做版本目录学的人写这样的东西,应该学习借鉴的。起码从体例上,我觉得有些方面不要说超越他,似乎还没达到。
程老师:应该可以这么说。
王锷:上次我跟刘蔷也探讨过这个话题,她也认可我这样的说法。所以您专门整理这本书,您也有自己的想法。也就是说,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书很多,给某个藏书家的藏书编一藏书目录,做一个目录书嘛,大不了注明是什么版本,或者是有序、有跋、藏书印什么的。而他详尽到里边的刻工,原版和补版的刻工,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事。
程老师:是。以我们今天的条件,现在各种工具书的出现、网络信息的丰富,对于这个书再进行补充和订正,可能会让他的学术价值更高、发挥作用更大一些。
王锷:我想因为您现在在校经处,拥有那么多的工具书,其实,比如说张先生他原来什么样,就在那摆着,他错就错了,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给它出校记,或者是后边出按语之类。我倒觉得您可以来做做这个事情,即使您没有那么整块的时间,可以带一个学生一起来完成。一起完成的话,一则可完善该书,二则可培养人,然后在前面写一篇非常好的前言,说清楚作为版本目录学的藏书志,为什么要这样来写,他的这种体例在藏书志的历史上,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,启示后人怎么做,我觉得更重要。
程老师:这个建议很好。
2016年摄于重庆图书馆前
王锷:似乎没看到有人对它有过很高的评价。
程老师:这说明它在学术界发生的影响不够大,按说应该很大。
王锷:我对它用得多,因为与八行本《礼记》有关。但是似乎没有人说这是很好的书,因为类似的书真的很多。你比如说丁丙的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,没有版本的更多信息,对吧?这个刘蔷搞的《天禄琳琅书目》,是有版本信息,藏书印是选一些,没有详尽地把刻工这些东西全部给弄出来。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的学术价值很大,对于后人来说,现在比如说是研究刻工,我们也要赖以查考的。比如说这个明代书的刻工要查考李国庆先生的书,这个宋元版书有赵振铎他们,也就那么几部书,但不是很全面,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要比他们全,信息量大,学术界重视不够。
程老师:泛泛地翻看,是认识不到它的好的,只有真正在某部书或某类书上下了功夫,尤其是注重它版本的学者才能真正意识到它的好、它的全面。
王锷:所以,我建议您重新做,可以使这部书发挥它的一个作用,给我们版本目录学界一个更多的一个启示,已经有这么一座丰碑在了,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真的建议您重新做,包括钱大昕的书,把它重新修订一下再出,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。
程老师:当时就是放在这个丛编里边,它是放在某一册的中间。如果是独立的一册,可能还好一些。
《山东著名藏书家》
王锷:你跟杜老师合作写过《山东著名藏书家》,请您来谈谈相关情况。
程老师:当时是齐鲁文化中心搞了一个《齐鲁历史文化丛书》,涵盖方方面面,共分100种。要求篇幅不要很大,要求通俗易懂、雅俗共赏。当时泽逊领的项目就是《山东著名藏书家》,但是一直到那边催,快要到交稿期限了,他因为忙于其他项目没有时间写,他就跟我说要把这个项目退回去。我说那不很可惜吗?我说我可以来做。他说你有时间吗?我说时间都是挤出来的。那就挤呗。当时我们大约就规划了写16个藏书家,从第一个王粲开始,到最后王懿荣、徐坊,写了16个。这里边包括赵明诚、李清照。我们当时的教学工作量非常大,我就一周除了上课,就收集资料,写成一个藏书家。当时电脑还很少,都是手写。收集资料也是手抄。那么最后我写成了稿子,去上课的时候,交给我们一个学生,他家有电脑,他会录入。等下一周,我再拿一篇新的给他,他把打印的上一个藏书家给我,我再改改,下一次再给他返回来。大约是16个藏书家,我写了是13个。泽逊没有时间,他写了3个,大致是这样。那么最后这个书出来了,反响还不错,但是大家想买买不着。现在这个书非常难找,因为当时是丛书里边的一部分,现在很难买到这个书。
王锷:这个书,您觉得主要有哪些特点?您自己作为作者来说,怎么看待这个书?
程老师:我感觉到山东人藏书,历史比较悠久。包括宋代的晁公武,是山东人。当时他在四川做官,当时四川的转运副使,叫井度。他家藏书非常多,当时他曾经说过,将来我的儿子,如果是这块料,我把书给他;如果不是,我要赠送给喜欢读书的人。最后,他就把书给了晁公武。汉末王粲,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,蔡邕把书赠给了王粲。在历史上有名的这种“蔡邕之赠”,都是赠给了山东人。这说明山东人好学,喜欢藏书。山东人在藏书这个方面还是非常有传统的,而且是代不乏人。清末四大藏书家,在江北,也只有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。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,关于山东藏书史,也很感慨,也为山东人自豪。
2015年摄于扬州瘦西湖
其实,有点遗憾的就是修《四库全书》的时候,山东献上去的书很少。我一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。什么时候有时间,可以找一找当时山东做这个事的官员,是什么人。而且《四库全书》七部,四部官方收藏,三部在江浙。山东作为齐鲁文化的发祥地,儒家至圣先师、亚圣都在这里,而山东没有一部,我一直觉得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。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,关于《四库提要》中的《离骚中正》这部书。这部书的作者林仲懿,是我的乡贤前辈,山东栖霞人。《四库提要》里边说,不知道作者林仲懿是何许人。《离骚中正》这部书山东大学有一部,是个清刻本。《离骚中正》,他用儒家的中正思想来解读《离骚》,这在《离骚》的解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。我认认真真地阅读这本书,这部书的最后一页赫然印着“栖霞林仲懿”。林仲懿是个解元,到了安徽去做官做了一年,挂绶而去。官不当了,回家读书做学问、刻印,喜欢刻印,所以他的书后面都刻了很多印,都是他自己刻的。赫然在目的“栖霞林仲懿”,四库馆臣说不知何许人也。我就在想,四库馆臣大概一看这个书名,《离骚中正》,就不以为然,大概把这个书连翻到底的耐心都没有。如果翻到底,怎么可能不知道林仲懿是什么人,是哪里人呢?所以我也在想,大概当时山东的官员对于国家要修《四库全书》这个事情不太重视。那么山东贡献不大,献上去的书不多,最终的四库七部书里边,也就没有一部落到山东这块大地上,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。所以就是说,在写这个藏书家的过程中,一个方面,就是对山东藏书的历史有了很大的认识。当然,写这个书的时候,王先生的那个《山东藏书家史略》,这部书给我们帮助也很大。再一个是,对于藏书史料、对于这些藏书家的传记资料,也全方位来接触,后来也写了相关的章节,在《藏书家》上也发了一篇关于王懿荣天壤阁藏书的文章。
王锷:目前反映山东藏书史的书籍,除了王先生《山东藏书家史略》之外,就是你们所写的《山东著名藏书家》,就这么两部书。似乎后面再也没有人再继续往下做,是吧?
程老师:所以现在回想起来,这个项目没有退掉,是很好的,挤一挤时间,也就做出来了。
王锷:这两种书,其实对于山东藏书史的研究,还有开创之功。
程老师:应该有,可以这么说。
王锷:我觉得,一个地方的藏书,是与它的刻书事业有关系的。您这一说我就想起来,明代的时候,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陈凤梧在山东做官,当时他在山东刻过《仪礼注疏》17卷。目前的学术界的主流的观点,认为《仪礼注疏》的经、注、疏、释文的汇刻,这是第一部。但是这个书是在山东刻的,后来书版在嘉靖五年的时候就送到了南监,到了南京去了。到南京去以后呢,闻人铨又刻过,再后来福建的汪文盛又翻刻过。他们这三个人刻的《仪礼注疏》,可以肯定地说是同一个源流,这是毫无疑问,我对过。这里边我想要说的就是,陈凤梧在山东刻书,《仪礼》除了刻注疏,他还刻过《仪礼》的经注。陈凤梧在山东刻书,版又送到了南监。换句话来说,起码从明代那个时代来看,山东的刻书事业应该是发达的。所以这种发达,也会给藏书带来繁荣。我倒觉得,将来如果有机会,这些方面还可以结合起来。您已经有很好的基础,可以再挖掘挖掘,把它再做一次。
程老师:唐桂艳博士,她的博士论文就是《清代山东刻书史》。
王锷:出版了吗?
程老师:刚出版,齐鲁书社,三巨册,后面附有索引。从正文到索引,都非常仔细。
王锷:杜老师的博士是吧?替我要一本吧。
程老师:替你要一部。
王锷:所以,我认为您做这个《山东著名藏书家》,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的。
程老师:当时我是积累了很多资料,可是这部书的要求呢,是要求通俗易懂。我一直想接着写,因为在写王粲的时候,王弼就是王粲的后人。就是王氏家族,王粲是三公之后,是世家。是世家便肯定有藏书,但是史料记载不多,我推测肯定是这样子。那么到了王粲的时候,他既好学,蔡邕又兑现了他的诺言,把一部分藏书给他。后来到他的儿子辈,到他的孙子辈,拥有的藏书就很多。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在当时搜集资料的时候,我感觉到,这应该是中国藏书史上最早的藏书世家。战国时候,像惠施藏书,苏秦也藏书,但是没听说他们的后人还在藏书。那么从藏书世家上来讲,我感觉到这个王氏家族应该是最早的藏书世家。曾经也有意要写这样的一篇文章,到今天也迟迟没有完成。当时搜集的资料还在。
王锷:那可以把它接着写出来,都有资料,也有思考,可以写出来。
《儒家者言》
王锷:程老师,就是我们认识十多年,每次聊,当然和杜老师聊得多,所以对您的科研信息掌握得不全面,采访可能有遗漏的地方,您还有没有补充的,再讲一点。
程老师:刚工作时参加过《中国历代辞赋鉴赏大辞典》,后来翻译过《儒家者言》这本书,是齐鲁书社出的。
王锷:哦,我没看到过这本书,不了解,请谈谈相关情况。
程老师:《儒家者言》就是把儒家重要经典里面的名言挑了几百条,然后就是我做了翻译。然后请一个美国人孟巍隆翻译,他现在在山东大学儒学院工作,汉语很好。他再根据我的翻译,再翻译成英文,齐鲁书社的目的是把它打入西方市场,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和智慧。这本书出来,反响也是很不错,叫《儒家者言》。
王锷:那也要送我一本哦,有的话。
程老师:送你一本,我找找看,这个书是零几年出的,应该是零七年。我回家找找看,应该有。他这个书有两个版本,一个是带英文的,它主要是往国外推销的;还有一个就是把英文翻译去掉。我的收获也是很大。但是这个工作看起来容易,事实上很难。比如说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怎么个翻法?它不好翻译。这个孟子的“大丈夫”说,这个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翻译出来不好翻,可是很费脑筋的。但我觉得这样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,销量也不错。
王锷:您的所作所为,我刚才还想问来着,就您上《论语》的课,也上《四书》导读的课,刚才您又说了做了《儒家者言》,这些儒家经典的思想对您有什么影响?
程老师:有影响。我觉得《论语》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。这部书被称为“人生智慧海”。年轻的时候,上大学的时候读《论语》,品味出来很少。随着阅历,随着你经历的事情越多,你越发的感觉到它确实是一部智慧之海。所以现在在一些场合,在一些座谈愿意讲《论语》,也是基于对它的认识,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讨论。
在80年代,,叫《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》。文献学的版块给了王先生。王先生就让我们几个年轻人来写。当时版本目录这一块,古代典籍的重要词条,是我写的,这也是我进入文献领域早期经历的一些事情,一些积累。
---未完待续---
小编按:2016年6月17日,王老师于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办公室采访程远芬教授,访谈稿由尼山学堂宋怡心、林诗丛整理,已经程老师、王老师审定。
责任编辑:子璋
文字编辑:越之
版式设计:子伃